
东经94.9度线上的格尔木市,盛夏时节六点钟时,天还没有亮透。为了躲开青藏公路的堵车高峰,在零点之前赶到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保护站,我们一大早就从格尔木出发了。
天阴得结结实实,铅灰色的云团低低地压在头顶。整个格尔木市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,大街小巷都静悄悄的。车窗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细霜,后备厢里层层叠叠塞满了帐篷、睡袋、矿泉水和压缩饼干。对讲机时断时续,司机师傅们安排着谁领队,谁压后,谁跟在中间。

格尔木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枢纽,扼守青海进入西藏的咽喉,也是进入可可西里的补给休整大本营。青藏公路正在拓宽施工,车队蠕行在无尽的施工现场,碾过碎石坑洼,走走停停,颠簸得直想晕车呕吐。
从格尔木出发5个小时,隐隐绰绰的山峰突然清晰起来,像从戈壁平地上长出来一样,昆仑山口就横在了眼前。短短160公里,海拔就从不足2800米抬升到将近4800米。
昆仑山口,索南达杰纪念碑静静矗立。纪念碑旁砂红色的雕像,高大而肃穆。我们下车,向这位因守护可可西里藏羚羊而牺牲的英雄鞠躬致敬。
 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雕像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雕像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,虚飘虚飘的。高原反应开始像窗外的景色一样,变得清晰而沉重。食物在胃里翻江倒海,寻找喷涌的突破口。脑袋像将要开锅的爆米花一样,感觉马上就要炸开。司机师傅提醒看看指甲盖,果然已经成了紫酱一般——这是血氧含量不足的明显特征。虽然带了血氧仪,但大家都克制着不敢使用。
按照医学常识,一般血氧饱和度低于90时,需要尽快就医。但假如真是低于这个数字,那我们是撤退呢,还是继续前进呢?所以,干脆就不看,实在忍不住了再说。
天渐渐地晴朗起来。青色的巨石,嶙峋突兀,一直垒到了天上,云雾在半山腰纠缠,和山顶的积雪连成一片。司机刘师傅一边开车,一边“客串”导游,从纳赤台,玉虚峰,一直讲到玉珠峰……
 行车途中,窗外的景色雄伟而单调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行车途中,窗外的景色雄伟而单调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窗外的景色雄伟而单调:直插云霄的昆仑山峰、线条分明的青色岩石、瀑布般直挂而下的冰川积雪……但没完没了的颠簸摇晃,越来越重的高原反应,让这些景物逐渐变得模糊,红景天的效果也都归了零。
迷迷糊糊中,听着师傅说到了不冻泉。看看海拔,4600米。一翻资料,说含氧量仅是平地的40%。再看看同事的嘴唇,果然都像茄子一样!
不冻泉是此行进入可可西里的最后一个加油站。车子加满油,简单休整一下后,我们继续前行。景色愈发纯粹单调,冷峻得仿佛看不到生命的痕迹。远处是连绵的雪山,冰川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圣洁的光芒。
 车队行车途中。新华社记者 卜寄傲 摄
车队行车途中。新华社记者 卜寄傲 摄
下午三点左右,车队驶下青藏公路,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。天空以一种近乎霸道的姿态撞进眼帘,纯净得没有一丝褶皱,低矮得仿佛踮踮脚就能摘下云絮,连呼吸都瞬间染上了高原的清冽。
阳光像被打碎的宝石,毫无保留地倾洒。渐行渐远的昆仑山脉若隐若现,如同神话里沉睡的巨人,用皑皑白雪编织的披风覆盖着身躯。
 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景色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景色。新华社记者 令伟家 摄
过了索南达杰保护站,就算真正进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。车子时而高高腾起,接着又俯冲而下,比过山车还要刺激。每个人都紧紧握着扶手,生怕一松手就被抛出车外。虽然带了制氧机,但每个人都极力克制着——听说,吸一次氧,就再也放不下了。
剧烈的颠簸,赶走了缺氧的迷糊。打开车窗,猛吸一口,仿佛就能闻到亿万年荒原的气息。展开手掌,凉丝丝的风轻轻划过掌心,好似大地在温柔地打招呼。
几只藏野驴在不远处悠闲地吃草,在草原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一只小藏野驴扬起脑袋,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些“不速之客”。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黑暗吞没了一切。除了汽车的灯,看不到一丝光。熟悉了城市生活的我们,第一次领略到了万古荒原的寂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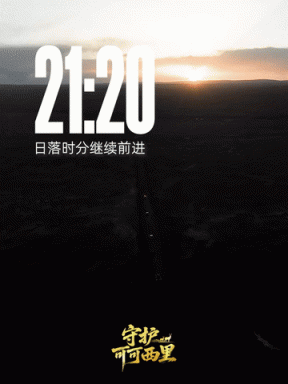
夜里十点钟左右,前方出现了若有若无的光点。司机师傅兴奋地提醒大家:“快到卓乃湖了!”
快到卓乃湖了!城市里司空见惯的那几点光,成了荒原上最让我们亲切的期待——那代表着文明、意味着人间烟火。从索南达杰保护站起,我们已经连续10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个人,没有看到一丝人类的印记。
 可可西里日落时分。新华社记者 卜寄傲 摄
可可西里日落时分。新华社记者 卜寄傲 摄
瞬间,我们忘记了高反的难受。可可西里的星空,已经拉开璀璨的帷幕。星星那么多,那么亮,那么近,满天星河,似乎就要倾泻下来。
300多公里、16个小时。深夜十点多钟,我们终于抵达卓乃湖保护站。
卓乃湖,一个被称为藏羚羊“大产房”的地方。生命在这里悄然诞生,也将被人们用心守护。
策划:钱彤
统筹:常爱玲、陈凯、令伟家
制作:于卫亚、史卫燕、焦旭锋
记者:令伟家、卜寄傲、刘雅萱
视频:刘思录、郭依格、邓寒思、杜笑微、张龙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1号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